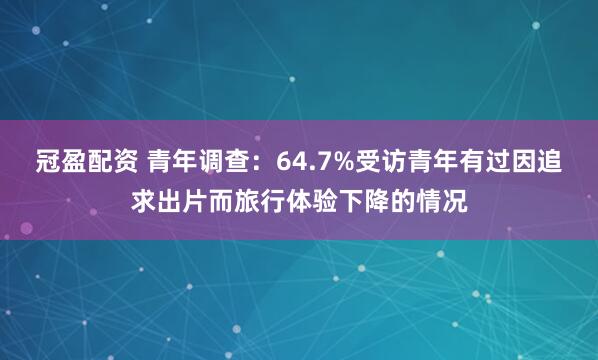日期:2025-09-24 00:46:4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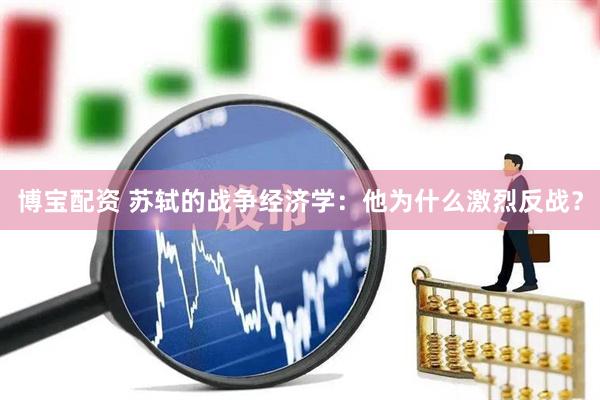
来源:市场资讯博宝配资
(来源:亮叔行动学)
苏轼的战争经济学。
01
一封“唱反调”的奏书
1077年,宋神宗即位十年,锐意进取,正打算扩大对西夏的战争。
朝堂之上,满是主战派的声音。宋军四处开疆拓土、接连小胜,年轻的皇帝更加自信:只要加大投入,就能彻底打败西夏,甚至进一步与辽国开战,收复失地。
一片胜利欢呼声中,却有人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。
在南都(今河南商丘),71岁的前任宰相张方平决定写一份反对战争的奏书,给皇帝泼一盆冷水。
因为年老眼花,笔力不济,他让弟子苏轼为自己代笔。
张方平是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,当年,他在主政四川时发现了“三苏”,把他们推荐给了欧阳修。这才有了苏轼父子后来的名扬天下。对于张方平,苏轼一生以门人弟子事之。
展开剩余85%这封《谏用兵书》,反映了他们师生两人共同的反战思想。那么,他们为什么都激烈反对战争呢?是因为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吗?
02
战争经济学
其实主要是基于经济计算,关于战争,他们算了三笔账:
第一,战争成本太高。
兴师十万,日费千金,内外骚动道路者七十万家。内则府库空虚,外则百姓穷匮,饥寒逼迫。
一场战争,每天消耗的钱财高得惊人。十万士兵出征,背后需要七十万户家庭承担运输、供应。对内导致府库空虚,对外则导致百姓贫穷匮乏。
远方之民,肝脑屠于白创,筋骨绝于餽饷,流离破产,鬻卖男女,熏眼折臂、自经之状,陛下必不得而见也。
远方的百姓,有的在战场上被刀枪砍杀、肝脑涂地;有的因为运送军粮耗尽体力,筋骨劳损。他们被迫背井离乡,家产散尽,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儿女。还有人被战火熏瞎眼睛、打断手臂博宝配资,最终走投无路上吊自杀……这些惨状,陛下您并没有见到。
比犹屠宰牛羊,刳脔鱼鳖,以为膳羞,食者甚美,死者甚苦。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,宛转于刀几之间,虽八珍之美,必将投箸而不忍食。而况用人之命,以为耳目之观乎?
这就好比屠宰牛羊,剖割鱼鳖,用来做成美味佳肴。吃的人觉得非常美味,但被杀的却极其痛苦。如果陛下亲眼看见它们在刀刃下号叫,在砧板上翻转挣扎,即便是山珍海味,您也一定会放下筷子,实在不忍再吃。既然如此,何况是拿人的性命来当作娱乐表演来看呢?
第二,风险太高。
上则将帅拥众,有跋扈之心;下则士众久役,有溃叛之志。
将帅手握重兵,容易滋生专横跋扈、不臣之心;下层的士兵长期服役征战,容易产生溃散逃跑或反叛的念头。
宋朝以军事政变开国,在防范武将上其实做得很成功,比如制度上重文轻武,比如喜欢任用太监来统帅军队。宋神宗后来发动“五路伐(西)夏”,其中两路大军的统帅都是太监。神宗本来计划用太监来做总指挥,后来在大臣的反对下,自己担任统帅,远程指挥。
这种制度安排,规避了“将领跋扈、图谋不轨”的风险,但是又增加了新的风险,那就是获胜概率很低。
若军事一兴,横敛随作,民穷而无告,其势不为大盗,无以自全,边事方患复起,则胜广之形,将在于此。
战事一起,为了筹措军费军粮,横征暴敛就会随之而来,百姓们饥寒交迫活不下去,就会揭竿而起。
第三,收益太低。
取空虚无用之地,以为武功,使陛下受此虚名,而忽于实祸,勉强砥砺,奋于功名。
高成本和高风险并不等于一项投资就是完全错误的!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指标:收益。
但是,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,对古人而言,耗费无数的生命金钱去征服那些偏僻蛮荒之地,既不适合种地,也收不上来什么税,更没有什么金矿银矿,完全是赔本生意。
且夫战胜之后,陛下可得而知者,凯旋捷奏,拜表称贺,赫然耳目之观耳。至于……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,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
就算侥幸取得胜利,看得见的是赫赫武功,看不见的是将士血流成河、百姓流离失所;听得见的是凯歌高奏,听不见的是孤儿寡母的痛哭声。
得到的都是虚名,失去的都是真实的生命和财富。
03
仁义道德与经济利益
张方平是北宋著名的财政专家。
他曾两度担任国家财政部长(三司使),政绩斐然。神宗上台后,最初就准备任用张方平来主持变法,解决国家财政问题。但张方平因为父亲去世,回家守孝了。
在这封反战奏书中,张方平、苏轼的逻辑,和我们对古人的认知不同,他们并不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反对战争,而是通过纯粹的经济计算。
这当然不是因为张方平、苏轼不重视仁义道德,而是因为,在反战这件事情上,仁义道德和经济利益,恰恰是一致的。
在他们看来,不要轻易发动对外战争,不要轻易耗费百姓的生命和钱财。既符合仁义道德,也符合大宋的经济利益。
义和利,仁义道德和经济利益,在很多时候,其实都是一致的。
仁义道德就是经济利益,你爱好和平,就有更大概率长治久安、经济繁荣;经济利益就是仁义道德,为他人创造价值是提高自身收益的主要方式。
04
胜利的狂欢与清醒的冷水
苏轼代张方平写这封反战奏书时,神宗皇帝正忙着开疆拓土,形势一片大好:
今师徒克捷,锐气方盛,陛下喜于一胜,必有轻视四夷,陵侮敌国之意。天意难测,臣实畏之。且夫战胜之后,陛下可得而知者,凯旋捷奏,拜表称贺,赫然耳目之观耳。
张方平和苏轼却在胜利的狂欢中感受到了恐惧,他们知道,此时意气风发的皇帝必然不会听自己的,但也许将来有一天,皇帝会想起这封奏书:
今陛下盛气于用武,势不可回,臣非不知,而献言不已者,诚见陛下圣德宽大,听纳不疑……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,必将哀痛悔恨,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,臣亦将老且死,见先帝于地下,亦有以借口矣。
如今陛下一心征伐,态度坚决得难以挽回,我并非不知道这一点。但我依然不停地谏言,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胸怀宽广,能接纳意见。而且我预料,陛下将来若亲眼看到用兵带来的危害,必定会感到悲痛悔恨,进而追究身边大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事先直言劝谏。我(作为臣子)即便年老离世,到了地下拜见先帝时,也有话能为自己辩解(没有辜负先帝托付、没有沉默失职)了。
四年后,1081年,神宗调动35万大军、20万民夫,五路伐夏,大败。
1082年,宋军在永乐城被西夏包围,损失士卒、役夫二十余万。“集中在永乐城中凝聚着变法‘富国’成果的金银粮草军用器械尽为西夏所有。”
(神宗)至永乐之败,颇思其言。
——苏轼《张文定公墓志铭》
人教人,教不会;事教人,一教就会。可惜代价太大了。
参考书籍:博宝配资
发布于:北京市51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